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的生态文学不断壮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实意识与人文关怀始终是推动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并且报告文学成为生态文学最早的突破口。1978年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大雁情》和1986年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是生态文学领域的“报春花”,这些作品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忠实地、准确地、富有艺术性地观察并反映人与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进入新世纪以后,生态文学快速发展,覆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生态诗歌遍地开花,网络文学的生态题材创作也渐入佳境。
地域特色的凸显是新世纪生态文学的显著变化,反映出生态文学逐渐细化、深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早期的生态文学创作表现出勇于尝试的探索精神,但有些也存在表面化、同质化的局限性,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往往被理解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在新世纪生态文学中,成功的作家善于开掘自己的生命经验,将心比心,接通地气,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个体生命、周围人群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状态,在天地人多维互动的生态关系中讲述美丽中国的故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人民在顺应自然的长期摸索中,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契合方式,这种生态智慧积淀成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成为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家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是建构生态文学地域特色的基础。譬如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诗意化的笔触礼赞了鄂温克族人充满灵性的浪漫情怀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他们与树木、驯鹿进行平等的生命交流,作品弘扬了敬畏自然、尊重弱小的悲悯精神。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种特殊的纪念,阿巴追寻文化根脉、重返精神家园的艰难选择,启迪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我的定位。刘亮程的生态散文扎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的一个小村庄,写出了独属于作家个人的生命境界,这是一个“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的世界,风塑造了这儿的生命形态,他的作品中回荡着吹到骨头缝里的风声,他的文字就像黄沙梁的每一种生物一样,也在顺应与抗击大风的挣扎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韧性与张力。沈念的《大湖消息》既关注洞庭湖区内生物的命运,记录了候鸟、麋鹿、鱼类、江豚的浮沉起落,也写出了江湖儿女飘飘荡荡的如水性情。《人间客》中的打鱼佬不愿意一网打尽,“要给鱼留一条活路”,自觉是“一条漏网之鱼”的女人决定“要留在这里做一条成群的鱼”,最终还是半生凄苦,就像一条落单的鱼。水边的人群与生物休戚与共,在奇妙的平衡中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
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文学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也包含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底蕴。孔子说:“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礼记·哀公问》)“天地合”是万物化生的前提。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敬畏天道时,他的回答是:“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天道的魅力在于创生没有止境,而且有自身的规律。儒家视野中的“生生”就是生生不息,而且充满变化,日新月异。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齐鲁文化的丰富资源,这为山东生态文学带来多种可能性。
在张炜的笔下,胶东半岛的一草一木、林中动物、水中鱼群都包含一种特殊的生命能量,他不仅诗意地描述了登州海角万物共生共荣的独特的自然生态,而且始终在思考如何建构一种健康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精神生态。从《九月寓言》到《河湾》,他对人与万物和谐互爱的精神家园的寻找,包含一种健全生态伦理的自觉,高扬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定居青岛的杨志军以感恩心态遥望他熟悉的青藏高原,他的作品始终饱含对生态问题的忧患意识。在其新作《雪山大地》中,以强巴阿爸为代表的支边人完全融入了当地牧民的生活,他们调动各方力量,齐心协力解决草原超载、生态危机、移民搬迁等问题,逐渐恢复草原的生物多样性。最近几年,山东作家在黄河题材创作中取得重要收获,张中海的《黄河传》向源远流长的黄河文明致敬,朵拉图和逄春阶的《家住黄河滩》、孟中文的《大河平野》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黄河滩区人民脱贫迁建的壮阔历程。山东的生态文学和山东作家的生态意识都深深地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又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情怀融为一体,自觉地汇入整体性的时代进程。
(作者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省作协主席)
来源 | 中国环境报
来源:生态环境部
2023-07-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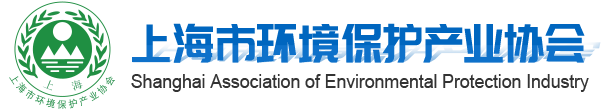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19303
沪公网安备31011502019303